坟墓是死者安息之所,然而汉墓之中,却拥有一条沟通生死的渠道。秦汉时代的人普遍相信,死亡不过是生命之形体与精神的分离。人死之后,灵魂升入天界,而形体则转入地下世界继续生活。因此,坟墓实际成为了死者的地下居所,人们在安葬死人时,需要将其生前使用过的器物及模拟物搬进墓穴,为其接下来在阴间的生活做好充足的准备。
民以食为天。既然生活还得继续,那么在坟墓中置入足够的饮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五十年前,湖南长沙市城东五里地的马王堆发掘出三座汉代墓葬。墓主是汉初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其中以一号墓出土的辛追女尸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马王堆汉墓中同样包括了丰富而全面的饮食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随葬品中出土的各种供食用的动植物遗存;其次是各种材料制作的不同形制的饮食器具;最后,墓中遣策(即随葬品清单)所记有关饮食的项目,正好为人们核对验证前两项内容提供了参照。这些发现为人们第一次直观地认识秦汉之际的中国人,特别是当时湖湘地区上层贵族的饮食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考察视角。

马王堆汉墓陈列展
一
马王堆汉墓中的食物遗存,大部分都是以留待烹饪的食材的形式存放的,其中首先是各种农产品。一号汉墓出土的农产品主要有14种,可归为粮食(稻、黍、粟、小麦)、瓜果(甜瓜、枣、梨、梅、杨梅)、蔬菜(葵、芥菜、姜、藕、大豆)等3大类,主要储存在边箱中的竹笥、陶鼎和麻布袋里。让我们先从充当主食的谷物说起。
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稻谷,根据形状,大致可分作4种类型。马01型,粒型狭长,形状与现代湖南省尚广为存在的某些晚稻品种(如红米冬黏、长粒籼糯等)相似。马02型,多数粒型类似华东粳稻,在湖南省现存的籼稻品种中很少见到。马03型,粒型长大,在湖南省现存稻种中极少见到,而与我国西北地区的粳稻品种(如米泉黑芒、养和堡白皮大稻等)极相似。马04型,粒型短而圆,接近于现存粳型晚稻和华东晚稻。以上,马01型属于籼稻,而其他三种属于粳稻。
水稻是原生于中国长江流域,经过史前农业驯化而来的一种世界级重要粮食作物。粳稻与籼稻是水稻在人工栽培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亚种。粳稻短而圆,多种植于北方。籼稻细而长,多种植于南方。而在长江与黄河流域,则往往粳稻、籼稻混合种植。所以马王堆汉墓中的稻谷,同时包含了分属籼稻、粳稻的几个不同品种。
根据考古发现,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已历万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先后发现了11粒距今一万年以上的古稻遗存。在稍后的澧县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发掘中,数以万计且形态完好的稻谷、稻米从古河道的淤泥中重见天日,证明湖南栽培水稻至少已有8000年的历史。而相邻不远的城头山古城遗址,还有一片已知中国年代最早的古稻田,其时代距今约有6600年。在中国,水稻从来都是南方人民最重要的主食。《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
与水稻不同,黍与粟是原生于中国北方的旱地粮食作物。粟,又称稷,也就是小米。黍,又叫糜子,去壳后称黄米,其形大于小米,性黏。先秦以来,黍和粟一直都是中原先民,特别是贵族阶层最主要的主食来源。但与水稻在北方被视为一种补充性主食类似,黍、粟在南方的情况也应如此。马王堆一号墓内,黍谷粒较多,仅混有少量粟粒。同时,墓中出土的陶盒、漆盒内还发现了黍、粟磨粉制作的饼,这说明这些粮食不仅可以充当主食,或许也有制作副食的功用。
在今人眼里,面食通常用小麦磨粉制作。即使要利用到小米面、黄米面,也需要在其中加入适量的面粉,依靠小麦中的面筋蛋白来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使之具备较强的塑形能力。不过,中国的先民似乎有另外的办法,纯粹依赖黍、粟磨粉制作面食。2002年,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曾出土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经鉴定,这碗面条是以黍、粟为主制作而成。近来学者借鉴饸饹的制作流程,利用淀粉糊化产生凝胶定型的方法,还原出类似的面条类食物。战国典籍《墨子》中也有关于饼食的记载:墨子对鲁阳文君说,有一个人家里牛羊满仓,厨子可以任意宰杀烹饪,吃都吃不完,即使如此,这人“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这则小故事,用来讽刺人之贪婪无厌,也说明饼食在中国自先秦以来,流传不绝。
这里墨子提到的饼,应当类同马王堆墓中发现的黍饼,而非由小麦磨粉制成。原因很简单,新石器时代晚期,小麦自西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烹饪小麦,都不经过磨粉加工,而是按粒蒸煮食用,故言麦饭。比起大米、黍、粟等粮食,小麦质地坚硬,蒸煮不易使其软化,且有糠皮不好去除,故而粗劣难食。及至秦汉之际,整个中原地区的贵族普遍厌弃食用小麦。当时,以小麦为主食的现象,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学者根据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人骨遗骸可知,东周至汉代,大量食用小麦的情况往往见于贫民阶层和殉人。《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少时家贫,与兄嫂一起居住,平日里都是乃兄种地养家,而陈平则读书游学,不事生产,反生得高大英俊,人问:“贫何食而肥若是?”这句话的意思是:都穷成这样了,是吃了什么东西长这么胖?其嫂讥讽谓“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糠核,即脱去糠皮的小麦。这等粗劣的粮食,也就是穷人无食者才会去吃。麦饭难吃,连带的是小麦的种植面积也有限。汉武帝时,“关中俗不好种麦”。但它能以相对更高的产量养活众多的人口,所以董仲舒借《春秋》之义,强调“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上书要求皇帝下诏让关中农民多种小麦。小麦在中国的命运,直至张骞通西域之后,才逐渐扭转。旋转小麦磨粉制作各种面食的技术,从西域传入。而旋转磨的适时普及也为小麦轻松地脱粒磨粉提供了物质条件。东汉时代,灵帝好胡饼,京城皆食胡饼,成为一时风尚。
不过,在此之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里,遣策登记的主食里,未经烹饪的有黄白秶(黍、粟米)各二石,稻白秫米、籼米各二石,已经烹饪的有黄白秶食各四器、稻食六器、麦食二器。其中,麦食叨陪末座,只占很小的比例,显示出它们在身为贵族的墓主食谱中的边缘地位。

湖南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二
马王堆汉墓里没有直接发现蔬菜的踪影,但有布囊所盛的葵种五斗。葵,也即今日民间俗称的冬苋菜,是锦葵科锦葵属的一种绿叶蔬菜,其茎、叶皆可食用。葵的原产地在东亚,除中国外,朝鲜、日本等地亦有分布。中国人吃葵菜的历史,少说也有三千年之久。《诗经·七月》“七月烹葵及菽”,这首西周初年的农事诗里提到,农历七月,正是煮食葵菜和大豆的时节。汉人有以葵、韭、藿(大豆叶)、薤(藠)、葱为五菜的说法,其中葵居首位。《灵枢经·五味》:“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除味甘之外,葵菜由于其茎叶中含有果胶一类的多糖物质,所以口感柔滑,且能促进消化。此外,葵菜种植面积广泛,抗虫害能力强,采收期长。一时吃不完,葵菜还可做成葵菹(腌菜)、葵干长期保存。这些优点,使得葵菜在汉代成为广为流行的蔬菜。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记有下葬品葵菜一筐。当时的大西北,也有葵菜的身影。居延汉简“十二菜畦,葵七畦,葱、韭菜共五畦”,葵菜是屯田士卒重要的蔬菜来源。葵菜还因为是喜光植物,故而成为了古代诗文中的常客。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的诗句,至今传诵。
元代王祯《农书》说:“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寒,味甘而无毒。”葵菜在中国的流行,至宋元盛极而衰。明代,葵菜百菜之王的地位,被由葑菜培育而来的白菜所取代。现今中国,仅有湖南等少数地区依然食用葵菜。冬天里,以油盐加水小煮冬苋菜,放豆豉调味,仍然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家常菜。
大豆在汉人的食谱里有些特别。汉人把藿归入五菜;而又把大豆,也就是菽,和稻、黍、稷、麦并列,称为五谷。一般认为,人吃了大豆后,不易消化,会引发胀气,所以只有穷人食用。从遣策登记的情况来看,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大豆算在了“五(谷)种”之列,主食部分则完全不见其踪影。这样来看,似乎它和小麦一样,都不是墓主喜欢的食物。与大豆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罐豆豉,其中拌有姜片。所以把大豆看成制作豆豉的原料——尽管还需要经历一次播种与收获——可能是其更加实际的用途。历史上,豆豉或许就在楚地最早出现。《楚辞·招魂》中提到以美酒好菜款待亡魂,其中诗句有“大苦咸酸”,大苦就是豆豉。到了汉代,豆豉的制作工艺传播开来。《史记·货殖列传》谈到,当时的通都大邑,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其中就包括千瓯盐豉。
制作豆豉,需要将大豆煮熟,然后加盐,酿制,经过微生物发酵,然后晒干保存。马王堆出土的豆豉,黑色,椭圆形,表面缩绉,与今天驰名的湖南浏阳豆豉在外形上几无差异。
马王堆一号墓中,还发现有芥菜籽可以充作调料。中国人很早就学会利用芥菜籽制作酱料,其中的辛辣味可以很好地去除鱼肉的腥味。《仪礼·公食大夫礼》和《礼记·内则》中都提到,宴席上的生鱼片,需要在旁边专门配上一份芥酱佐食。有时,吃生鱼片搭配芥酱也需讲究时令。因为,《内则》也说“脍,春用葱,秋用芥”。这可能与农作物种植生长的时节相关,芥菜籽通常在夏、秋季节收获。湖南自古就是水乡,各种水产品在当地居民的食谱中占据重要内容。作为水产伴侣的芥酱,自然也必不可少。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食用芥菜,走上了丰富多元的道路,培育出如根用芥菜(大头菜)、茎用芥菜(榨菜)、芽用芥菜(抱儿菜)、叶用芥菜(雪里蕻)等各种品类。今天,芥菜籽已经很少见于湖南人的餐桌了,后者发现以姜和紫苏搭配水产更是一绝,但当地的重要食用油——菜籽油,依然源自芥菜型油菜籽的炼制。芥菜其实从未远离湖湘饮食。
马王堆墓中发现的水果,多为中国原产,如甜瓜、枣、梨、梅、杨梅、枇杷、橙、柚等,最后三种仅见于三号墓。这其中值得说说的,主要是枣和甜瓜。中国人种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诗经·七月》“八月剥枣”,意味着西周初年已经开始栽培枣树,并能够定期采摘了。枣是含糖量最高的水果之一,这使得它在糖分匮乏的古代,成为一种可贵的食物。《礼记·内则》说儿子侍奉父母,媳妇侍奉公婆,要用红枣、栗子、麦芽糖和蜂蜜来调和各种饮食的滋味。《周礼》之中,枣和桃、栗子、榛子等干鲜果实一起,成为酒席助兴的佳品。《仪礼》记载,诸侯国行聘礼时,受访一方要用筐盛着蒸熟去核的红枣慰问来使。无论内外,家事和国事之中,总是少不了枣的身影。红枣对于一个秦汉贵族的饮食而言,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红枣凭借着耐储藏和高糖分的特性,成为了对抗饥荒的主力。苏秦以六国合纵说燕文侯,就曾提到“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当然,说红枣、栗子完全可以替代粮食,这只是战国策士夸张的修辞。但燕文侯最终动心,“请以国从”,可见其中必然也有着相当的真实性。更具说服力的是,在北朝灾荒战乱频发的年代里编纂的农书《齐民要术》把枣放在诸水果中第一个加以介绍,详细解释了收枣、晒枣、干枣,以及制作枣油、枣脯等各种方法。
红枣之外,中国人自古还是吃瓜爱好者。在西瓜在五代时由西域传入之前,中国人吃的都是甜瓜,也叫香瓜。尽管这种黄瓜的近亲,原产地和西瓜一样,都在非洲,但甜瓜远在4000多年前,便率先抵达了中国的东部。上世纪50年代,浙江吴兴钱山漾属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两枚甜瓜子,除了稍小一点外,外形与今天的瓜子无异。甜瓜在中国,依照黑河——腾冲分界线被分为薄皮甜瓜和厚皮甜瓜两大类。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哈密瓜,其厚厚的瓜皮明显有利于避免瓜瓤水分的蒸腾。先秦时期,中国人围绕着吃瓜,发展出了等级森严的礼仪。《礼记·曲礼》说为天子削瓜,削去皮,先切成四块,然后横切,盖上细葛麻巾;为国君削瓜,削了皮,先切成两块,然后横切,盖上粗葛麻巾;为大夫削瓜,也削皮先切两块,再横切为四块,裸露不盖巾;士人只削去瓜蒂,而一般民众拿起就咬,不削不盖。总体来说,人的等级越高,吃瓜的流程就越繁琐斯文。尸检结果显示,辛追消化道内尚有未及消化的瓜子百余枚,这说明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从容吃瓜。只是不知她在这种从容进食间是否遵循了上述礼仪。
三
粮食蔬果之外,丰富量大的肉食,更是马王堆墓中饮食水平的直观体现。一号墓、三号墓中发现供食用的随葬肉食品,计有兽类6种(牛、羊、猪、华南兔、犬、梅花鹿),禽蛋类15种(雁、天鹅、鸳鸯、鸭、竹鸡、家鸡、野鸡、环颈雉、鹤、斑鸠、火斑鸠、鸮、喜鹊、麻雀、鸡蛋),鱼类6种(鲤鱼、鲫鱼、鳜鱼、刺鳊、银鲴、鳡鱼)。这些肉食品种多样,广泛性上远超今人食谱。但其中仅有少数(牛、羊、猪、犬、家鸡、鸡蛋)由畜养获取,而四分之三的肉食品类源自渔猎。它们大多都是过了初加工,然后被置于竹笥下葬;少量已经被烹制成菜肴,装在食器中。
猪和狗大约是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总能发现这两者的踪迹。小农经济下,每家每户在种田之外,利用残羹剩菜养上一两只猪和狗,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始终未曾改变。猪和牛、羊一起,很早就成为祭祀、饮宴最重要的肉食来源。除去人们熟知的,古人常以牛、羊、猪各一头为一太牢,进行高等级的祭祀活动之外,高等级饮宴,最核心的主菜由七鼎构成,分别是牛、羊、猪、干鱼、腊、肠胃,以及猪皮。除了干鱼,其余六鼎皆出自牛、羊、猪三牲。
古人也有六牲的说法,即在牛、羊、猪之外,另加犬、雁、鱼组成。狗在最初,也是常见的肉食品种。《仪礼》的燕礼和乡饮酒礼都提到了烹狗为菜的细节。孟子对梁惠王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和猪、鸡一样,狗便于喂养、繁殖能力强,且易于宰杀,是一个平民家庭非常容易获取的肉食来源。秦汉之际,社会上出现了职业狗屠,可见狗肉的需求旺盛。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聂政,以及刘邦手下大将樊哙,都曾是职业狗屠。直至东汉,墓葬内的画像石上仍有不少画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屠宰加工狗肉的细节。

汉画像砖的右端展示了汉人杀狗的画面
大雁自先秦起,就是社交上的高级礼物。《周礼》中提到,初为士者,将大雁作为礼物献给王,然后由膳夫烹饪后请王食用。雁有时也是大夫所进献的礼物。汉代典籍《白虎通》的解释是,大夫的职责在于奉君命出使四方,其一举一动应该能够自我端正,像大雁成行成列飞行一样。大雁还是传统婚礼第一步,纳采提亲时的礼物,以其一夫一妻,象征着婚姻和美。
学者指出,以雁作为一种高档礼物并广泛应用,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习俗。其实,不止大雁,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十余种禽类,都可以作为射猎文化曾在中国盛行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对禽类滋味的欣赏,有时集中于其脚掌中心的那一点刁钻的筋骨组织。《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貛貛是传说中的一种鸟。与猩猩之唇相对,貛貛之炙也不是什么“烧鸟”之名,清代学者王念孙说“炙读为鸡跖之跖”,大约就是当今人们吃的掌中宝。历史上,天鹅炙、鸮炙,也就是天鹅掌中宝、猫头鹰掌中宝,都曾经入选过美食“八珍”之名。
与禽类一样,墓中的鹿肉尽管数量众多,应当也是射猎所得。《吕氏春秋·知分》:“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鹿这种生物曾在山林间成群出现,又无攻击性,是上选的猎物。秦汉时期,鹿和野鸡、兔子一样,是人们外出打猎最习见的野味。《史记·田叔列传》就提到任安外出打猎,常常把猎获的麋、鹿、雉、兔等分送与同行者。西汉末年,人们开始尝试圈养鹿。据王充《论衡》记载,蜀地有一富商想要出钱让大儒杨雄把他的姓名事迹写进《法言》。但杨雄不听,骂说:“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圈养的鹿在当时尚是新奇之物,富人不讲仁义,和圈养的鹿一样,都失去了天性,不值得肯定。《齐民要术》引东汉氾胜农书,讲到用同等分量的麋、鹿、羊屎混合制作肥料。此时的圈养之鹿,至少不亚于羊群数量。不过,猎鹿的传统并不曾中断。汉末王褒《僮约》要求仆人能够“登山射鹿,入水捕龟”。长沙走马楼吴简记载的实物税“户调”包括调鹿皮、调麂皮、调水牛皮等,这说明晚至三国,长沙周围仍然有大量鹿群存在。一号墓遣策记载了丰富而多样的鹿肉饮食,像鹿臇(音卷,一种少汁的羹)、鹿肉芋白羹、小菽鹿肋白羹、鹿䑆(里脊)、鹿炙、鹿脍、鹿脯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湖湘人民对于鹿肉格外喜爱。
除了陶鼎、陶罐、漆盘等炊具或餐具中保存的成品菜肴外,马王堆墓中发现的肉食,多是经过初加工后,放入竹笥中保存的半成品或预制品食材。这点与前文谈及的农产品不同,它包括了切分、归类以及初步的加热处理。像牛、猪、鹿、狗等肉牲,一般不会整头收存,而是按照肋条、肩胛等部位,分割后装入竹笥。例如一号墓324号竹笥装有狗肋骨63条、胸骨20余块,研究者判断它们至少取自3条家犬;226号存牛右肩胛骨;324号存梅花鹿左侧膝盖骨;231、318、14号三个竹笥分别存有猪的头骨、四肢和肋骨,经鉴定,系一整只初生两月左右,体重5—6斤的乳猪剖分而来。先秦两汉时代,大中型牲肉往往是先一分为二,然后将左右胖(音盘)进一步按照肩、臂、前肢、股骨、后肢、脊骨、胁骨等部位切割,以备烹饪。这和遣策的记载也可以对应起来,如其中有牛肋炙一笥,犬肩一器等。
部分竹笥的签牌显示了食材已经过了初步的烹饪。如一号墓227号竹笥签牌曰“濯豚”。“濯”指的是将切分为小块的食材,放入开水中快速烫熟,有类今天的水爆、汆烫。“濯豚”就是开水汆乳猪肉。227号竹笥里摆满了用竹签串好的猪、羊、狗、鹿遗骨,显示出制备的食材实际不止猪肉一种。竹笥里,小型食材往往都串以竹签保存。331号“熬鳨笥”存放的是鸳鸯、竹鸡、喜鹊等各种小型鸟肉串。所谓“熬”,是指把酱和入食材,通过加热逐渐收干其中的水分。328号存放的是带有竹签的鲤鱼、鲫鱼、刺鳊、银鲴等中小型鱼类。现存54根竹签,有41根的一端有火烤导致的焦黑印记,328号无疑是一个烤鱼笥。
四
上文以食材为中心的分析,可以大致勾勒出马王堆汉墓主人生前的饮食结构。他们的主食以稻米为主,辅以黍、粟等优良的旱地粮食作物。一部分黍、粟还可以磨粉制作成饼一类的副食。少量小麦作为一种补充性主食存在。果蔬方面,甜瓜、枣、梨、橘、柚等丰富的本地水果带来了优质的酸甜风味来源。葵菜自古就是湖湘人民喜爱的蔬菜之一。它和遣策记载的芹菜、芋头、莲藕、竹笋等一起,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碳水补充和优质的植物蛋白质。此外,姜盐豆豉和芥籽证明湖湘饮食自古就和辛香料紧密相伴。马王堆墓主的肉食来源非常广泛,在家畜、家禽已经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食之外,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依然很多。这些都显示了秦汉之际,湖湘地区上层贵族的饮食营养状况。和现代人相比,他们食用的主食、肉类更加多元,但蔬菜和水果范围则相对较窄。
最后,我们还可以结合墓中的饮食器具以及遣策中的菜肴,谈谈当时的用餐形式。秦汉以前,中国人席地而坐。与之相适应,当时采用的是分餐制进食。食物按个人份分装在餐具里,置于案上,送至食客面前。东汉梁鸿、孟光夫妻恩爱,妻子孟光每餐做好饭,最终都是举案齐眉拿给夫君,有点像今天快餐店盛食物的方式,但庄重很多。
《礼记·曲礼》记载的案上盛食物的礼仪是,左边放带骨的熟肉,右边放切片的熟肉,米饭放在人的左边,羹汤放在人的右边。肉丝、烤肉靠外些,醋、酱靠里些。蒸葱安置在最外边,酒浆安置在右边。如果放干肉条,要弯曲部分在左,末端部分在右。马王堆一号墓里发现了两件漆器食案。其中之一出土时,上置小漆盘五件,漆耳杯一件,漆卮两件。小盘内盛食物,耳杯上有竹筷子一双。这应该是当时湖湘地区贵族饮宴的摆盘方式,与《曲礼》里讲的中原文化不同。

马王堆出土的一整套食器摆盘
案上的食物,具体来说,可以分作食、饮、膳、羞四大类。食指主食,由各种谷物蒸煮而成。离长沙不远处的沅陵虎溪山汉墓,时代和墓主身份都和马王堆汉墓十分接近,其中出土的《食方》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食谱。根据学者复原,两千多年前湖南人制作主食,需要先淘米,然后蒸制、放凉,如此反复三次,方才能够做出好的米饭。汉代盛行用釜煮物,上面加个漏斗状,带有透气孔的甑,便组合成蒸饭的工具。马王堆遣策有黄秶食、白秶食、稻食、麦食等多种主食,大概都是按照《食方》上的程序制作的。
饮即饮料。汉代酿酒不经过蒸馏工艺,所以酒精度数普遍不高。东汉经学家郑玄说《周礼》“饮用六清”,依清至浊有水、浆、醴、䣼、医、酏六种,看来当时的饮料主要依据液体的清澈程度分类。考古学者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钫、钟等酒器中发现了酒液残渣,年深日久,已无法鉴定其种类。遣策所记,则有白酒、醖酒、醝酒、米酒四种。《礼记·内则》中,酒有清、白二种。相对清酒而言,白酒当是酒体浑浊发白者。米酒,又称醴酒,也就是俗称的甜酒,酒精含量极低。醖酒、醝酒情况不详。前者可能是经过二次发酵酿造而成。
膳是席间主菜。牲肉被置于鼎中经过长时间炖煮,最后骨肉相离,形成一锅浓厚的肉汁,就是羹。羹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一方面肉中的蛋白质经水解转化为氨基酸,另一方面水是极佳的溶剂,可以让厨师调和五味,使之融入食材,最终创造出一种平衡和谐的味道,就是鲜味。《左传》中,晏子提到“做羹汤重在讲求和谐,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中餐讲究有味使之入,无味使之出,食材内外滋味变换最终导向的是对和谐之味——鲜味的追求。西方饮食传统中没有鲜味的概念。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弄清了鲜味的原理并发明了“旨味”(umami)一词之后,方被英语借用。因为主菜的缘故,马王堆汉墓中羹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根据遣策记载,一号墓和三号墓下葬了不同种类的羹共达54鼎之多,如有牛首䔯羹、羊䔯羹,是以肉类搭配腌渍韭菜。又有清炖的白羹,如鹿肉鲍鱼笋白羹。此鲍鱼不是海产,而是腌咸鱼。今天湖南还有所谓鲍腌鱼的菜品,其制作方法同样需要用盐腌制鱼肉。此外,芹菜、蓬菜(蒿类)、葑菜(芜菁)、苦菜等都可以与肉同煮,做成芹羹、蓬羹、葑羹、苦羹。马王堆一号墓中发现了一个漆鼎,里面盛有藕片半鼎,对照遣策,它应该是鲜鳜藕鲍白羹或鲫藕肉巾羹中的一种。
羞的原意是进,进献的是主菜之外的精致菜肴。这类食物,制作方式多样,用材不拘一格,因为数量众多,所以又叫庶羞。马王堆遣策里的庶羞有脍、脯、腊、膎(音携)、胾、炙等几大类。脍是刺身,以鱼最常见,需要搭配芥酱使用,也有牛脍、羊脍等。脯是薄片的干肉,如牛脯、鹿脯等,和今天的肉脯区别不大。腊是指小型动物做成的全干肉,比如腊兔。干鱼肉叫膎,遣策中有鲫膎、鲤膎。肉煮熟之后切片叫胾,像犬胾、豕(猪)胾等。炙是烧烤,不仅有肉,还有内脏,比如犬肝炙。《礼记·内则》有一个菜叫肝膋,被认为是《周礼》的“八珍”之一,制作方式便是用网油蒙在狗肝上炙烤。
食、饮、膳、羞四者之外,还有两类很重要的食物。一者是酱,古人吃肉得蘸酱,依靠腌渍酱料的盐以及发酵带来的风味调味。酱料或用肉或用菜,故遣策有酱、鮨(鱼肉酱)、臠(带骨肉酱)、菹(腌菜)等等之别。酱料之外,还有糕点,像蜜糗、粔籹、餢飳、卵餈之类。蜜糗、粔籹是用米麦调入蜜熬煮制成。卵餈就是鸡蛋黏米饭。这些糕点和前文提及的水果,主要出现在需要喝酒的场合,可以大大提升宴席的丰盛程度。

马王堆出土“君幸食”漆盘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食器、酒器之上,常题有“君幸食”“君幸酒”的字样。这是汉人的习俗,意在请君享受饮食之乐。人死不能复生,精致而丰富的饮食与器具埋入地下,逝者无福享用,意外地使今人一饱眼福,从精神上享受了这顿大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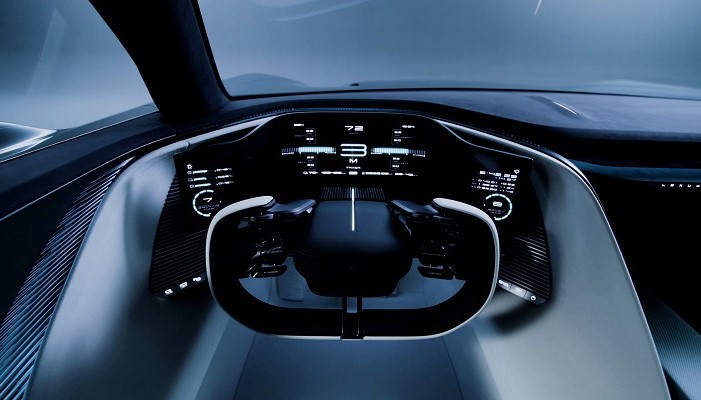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