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维克多·雨果作为最顶尖的文学大师都有着崇高的声望,尤其是他的两部杰作——《巴黎圣母院》(1831)和《悲惨世界》(1862)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着显赫地位(百度AI根据多个权威来源的整理,“世界十大名著”的各类评选中只有五部作品处于高频入选行列,雨果的这两部代表作牢牢地占据了其中的两个名额)。但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文学世界之外的雨果同样令人惊叹,因为他不只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划时代的小说家,他还是一位创作了超过3500幅画作的杰出画家(甚至被视作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先驱),一位终生致力于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顽强斗士(即便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涯中,他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艰难抗争),一位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化并热爱收集中国艺术品的装饰艺术家(他的著名散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1861)饱含着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赞誉和热爱,以及对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的强盗行为的深深谴责)……在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创作生涯中——无论是文学世界的内或外,雨果都以旺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澎湃的激情、先锋的姿态、深刻的洞见及卓绝的品味,书写了法兰西历史和文化的一段不朽传奇,也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思想、精神和文化遗产。

奥古斯特·罗丹制雨果半身像
画家或隐秘的激情
在文学的浩瀚星海中,许多大师级作家都对绘画怀有浓厚的兴趣,如歌德、卡夫卡、黑塞、泰戈尔、鲁迅等等,但能达到相当成就的却寥若晨星,而雨果正是这极少数之一。与他声名显赫的文学成就不同,绘画对于雨果波澜壮阔的人生而言,乃是一个内心的事业,或曰一份隐秘的激情。尽管雨果声称绘画只是“在写两节诗的中间,得以轻松一下”的消遣,但其在绘画艺术上所倾注的持久的心力,丝毫不逊于其在文学创作和政治事业上的巨大热情。学者程曾厚就雨果传世的画作数量,曾向巴黎橘园美术馆前馆长皮埃尔·若热尔请教,而后者经过多年考证断言约为3500幅。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世界级文豪,这一绘画创作数量是极为惊人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在致雨果的信中曾赞叹道:“倘若您立志成为画家而非作家,您的成就将超越这个世纪的所有艺术家。”
值得一提的是,雨果的绘画生涯与其旅行生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19世纪30年代莱茵河畔的那些旅行开始,雨果开启了自己的绘画生涯。十年间,雨果数次造访莱茵河,并用画笔快速记录下那些沿途的景物。不过,雨果那些天马行空的笔触和随心所欲的涂抹,与其说是记录现实中的风景,不如说是在记录心灵的风景——这些画作所描绘的莱茵河远远超越现实——雨果凭借纯熟的绘画技巧,赋予了这些奇特的画作以一种戏剧化的艺术效果。在1939-1940年沿着莱茵河流域的一次漫长旅行中,他找到了一个令他钟爱并能为之倾注想象力的创作主题:“古堡”——耸立在河畔嶙峋的山巅之上的中世纪城堡。此后七年,雨果迷上了用画笔描绘古堡。这一时期,雨果很少写作,并停止了公开发表政治言论,他在文学上被抑制了的创造力和消失的政治激情,在绘画艺术中得到了完美的释放。同时代的诗人兼画家泰奥菲尔·戈蒂耶以行家的眼光欣赏和推介雨果的画作:“他在这些浓重粗犷的幻想作品中,擅长把戈雅的明暗效果和皮拉内西的恐怖建筑糅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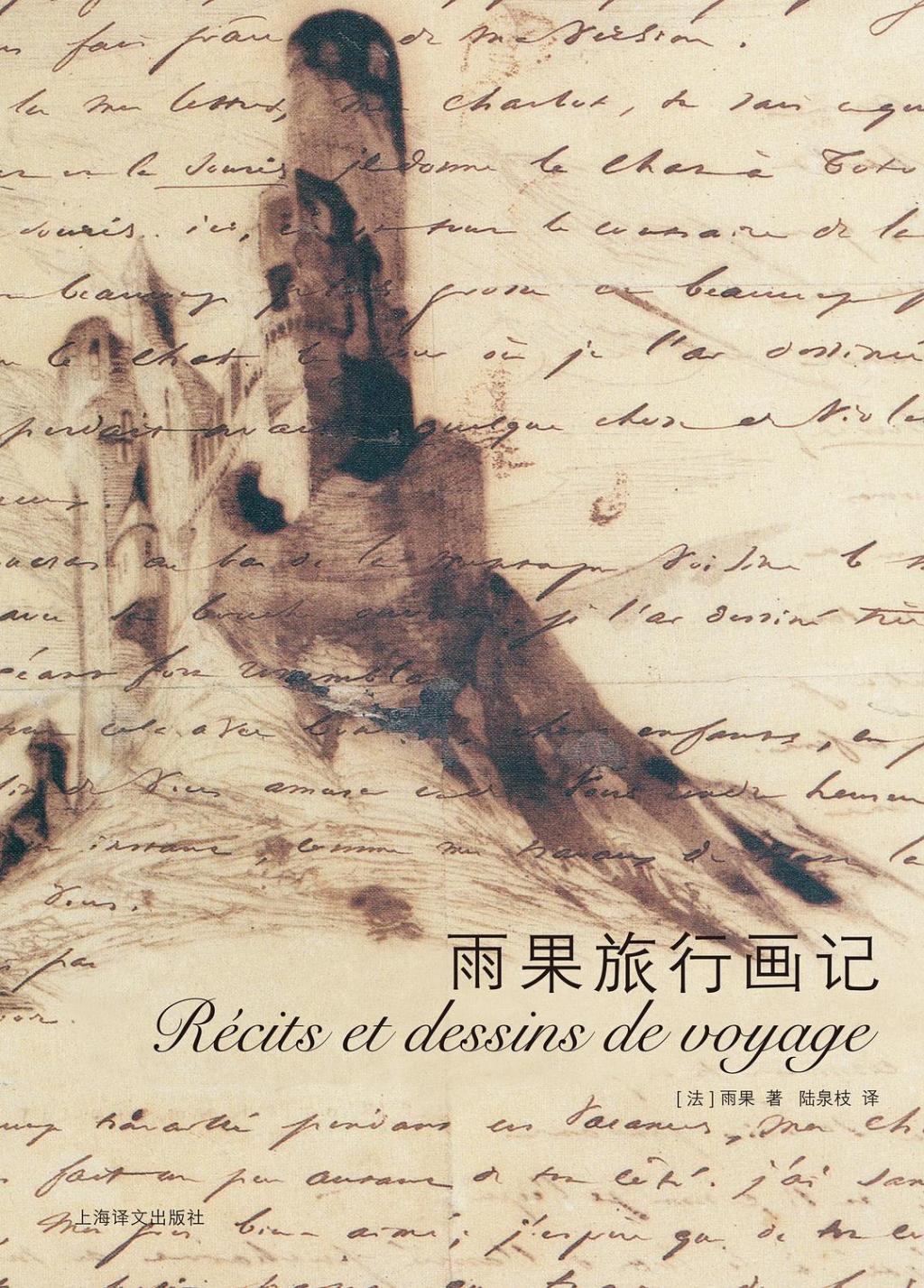
《雨果旅行画记》
相较于幽深蜿蜒的莱茵河,更让雨果心潮澎湃的是大海。1836年游历布列塔尼期间,雨果看到汹涌浩瀚的大海时喜不自胜,他急切地赤身奔向大海,“海浪每次把我包围,并将我冲到泡沫之中,那都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雨果对于大海的这种奇特情怀,或许正是罗曼·罗兰所谓的“海洋情感”。在雨果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海洋无处不在。海洋的力量和规模成为衡量这位作家、同时也是视觉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天才的艺术创作的重要尺度。1864年,雨果在莎士比亚诞辰300周年演讲中的一句话似乎最能代表他的心声:“似乎只有海洋是个足够广阔和雄伟的对手,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
大海在雨果的流亡生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855年开始,海峡群岛的根西岛成为雨果近二十年流亡生涯的居住地。在此期间,这个孤独的伟人常常面对大海,与渔民和水手擦肩而过……并从这个海上窗口写作和绘画。1857年,雨果创作了描绘海洋的绘画杰作《我的命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狂风正卷起巨浪袭来,一条小船飘摇在浪尖,上空一缕青烟随风而散——钢笔墨水和水粉的交叠使用看似随心所欲,却是雨果“奇异的杂糅”的创作技法的一个缩影,正如他在给诗人波德莱尔的信中的自白:“我只是在这些画里混合用上点铅笔、木炭、乌贼墨、煤粉、炭黑,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才能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此外,雨果借风雨飘摇的小船与滔天巨浪的激烈争斗,来承托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那股不屈不挠的豪迈之气跃然纸面。
在雨果看来,没有大海,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它是感知和感受人类存在的脆弱性及其真实维度的重要场域,并使我们能够在几个不同的宇宙之间建立起联系。经过在根西岛十年流亡生涯的经历、感悟与沉潜,雨果于1864年开始创作一部关于海洋的小说,这部不朽的杰作只花了短短的十个月即告完成,它就是著名的《海上劳工》——一首对海洋和“海上高贵人民”的颂歌。作家以一艘名为“杜朗德”号的汽船为引子,以此唤起人们将蒸汽引入海上运输的纪念。雨果为这部新小说专门绘画了一系列以海洋、船只、灯塔和沉船为主题的水洗画插图,共计36幅。大海的狂暴、包容、奇异和浩瀚,在一个个充满人性的故事中得以展现,而这些出色的插画作品与这部小说可谓相得益彰,令人惊叹。
痴迷政治者或自由斗士
随着1831年《巴黎圣母院》的出版问世,年仅29岁的雨果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和深刻的思想。在雨果的带动下,这股浪漫主义文学的潮流席卷整个法国文坛,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然而,对于雨果来说,文学上的成就并不能满足他想要成为“精神领袖”的终极理想。而立之年后,雨果常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不能发挥作用而焦虑不安。事实上,他的政治野心曾一度空前膨胀,渴望跻身于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可在当时,一位作家若想成为议员,必须先考上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
就这样,雨果接连四次向法兰西学士院发起“冲锋”,均以失败告终。第五次冲击时,恰好一个院士离世而空出一个名额,加上有大仲马相助,雨果终于得偿所愿。这时,他的政治野心已人尽皆知,一位亲王夫人幻想自己成为法兰西女王时拟定了“内阁名单”,排在第一个的“作战部长兼议会主席”就是雨果。不过,雨果后来的政治之路十分坎坷,他最终实现当选参议院议员的理想时已是74岁高龄,但自从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转而赞成共和制之后,雨果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斗争。50年代中期,雨果甚至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并在《惩罚集》《小拿破仑》和《一桩谋杀案》等一系列作品中谴责专制、政变和篡位。这位早年的政治痴迷者,最终活成了一代自由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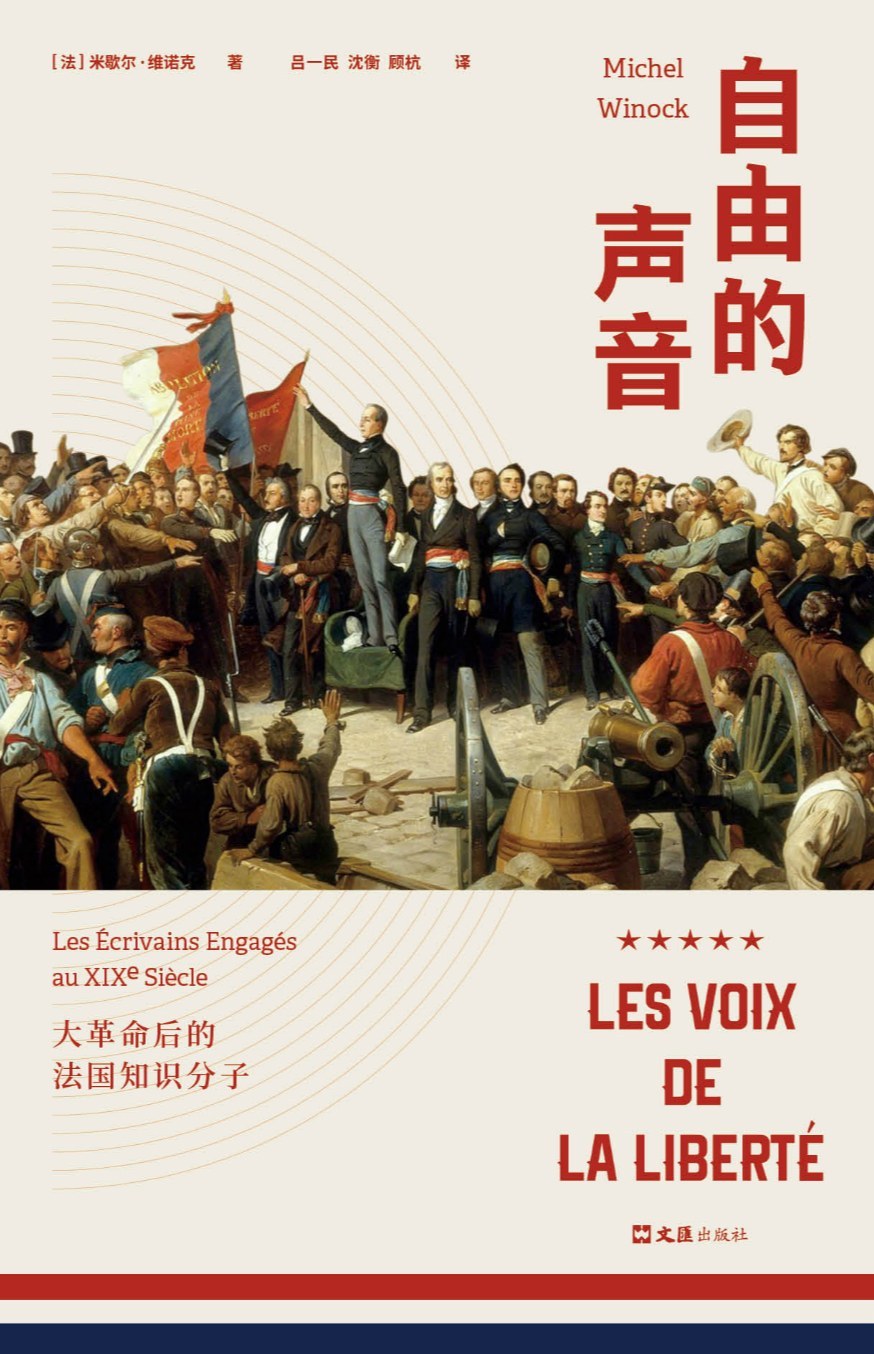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巴黎公社时期,身在布鲁塞尔的雨果对公社既同情又不理解。公社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大肆屠杀,他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受迫害的公社成员,开放自己的布鲁塞尔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在所有参议院议员默不作声之际,雨果以振聋发聩的激情打破了会场的沉寂,再次为“经过长期围攻依然泰然自若”却被取消首都称号的巴黎辩护。尽管他要求给予公社成员完全大赦的主张只获得九位同僚的支持,当时,图卢兹的共济会仍向他表示了共和派的感谢:“对于具有知识和道德的法国来说,你永远是伟大的诗人、充满勇气的公民、雄辩的思想家、那些最伟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则的代言人。”这位年过七旬的自由斗士坚持不懈地要求大赦,直至1880年7月大赦最后获得通过。
同样让雨果挂念于心的,是被奴役民族的独立问题——他一再为受到土耳其压迫的塞尔维亚人辩护。在1876年8月29日《致塞尔维亚人民》的演说中,雨果呐喊道:“让那些杀人的帝国灭亡吧!控制那些狂热和独裁的言论吧!打碎那些具有威胁性的迷信和教条的枷锁。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屠杀,不要再有蹂躏,而是要思想自由、贸易自由,要博爱。和平难道如此困难吗?除了建立欧洲共和国、大陆联邦,没有别的政治选择。”同年9月,雨果再次向民主派的代表大会提出,一定要有共和国的纪念日。在他看来,以下就是可以打碎枷锁和链条的至高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识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对死亡的解脱;自由的人,自由的灵魂。”
事实上,1848年革命后的雨果致力于所有自由的事业——大赦、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市长选举的逐步恢复,建立行业协会的自由、确立世俗和免费的义务教育、离婚自由的恢复……在雨果去世时,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在自由方面能与法国媲美?在几年的时间里,曾蒙受耻辱、令人失望、受人中伤的第三共和国,被置于受到《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以及一个世纪动荡历史激励的自由民族的基础之上。如今,当人们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挖苦19世纪的文学政治时,我们依然要感谢像雨果这样的自由斗士所留下的珍贵遗产,正如法国史学名家米歇尔·维诺克的忠告与提醒:“我们依然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仔细审视雨果文学作品的那种独特的创造力,其实与他为争取自由所作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尤其是晚年的一连串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括《凶年集》(1872)、《九三年》(1874)、《一桩谋杀案》(1877)、《历代传说》(1877/1883)、《精神的四种风向》(1881)、《多尔格玛达》(1882)等,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著作、散文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新上演或重演的剧本也大获成功:根据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剧本于1878年在圣马丹门剧院上演;同年,莎拉·贝纳尔再次主演《埃尔纳尼》《吕伊·布拉斯》以及1879年改编的《巴黎圣母院》,1882年《国王取乐》再度上演……所有的作品中都浸润着雨果“以自由为本”的灵魂,以及无处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
装饰艺术家或中国迷
许多中国读者在读到《巴黎圣母院》或《悲惨世界》前,都是通过九年级语文课本上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认识了维克多·雨果。雨果在信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地谴责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行径,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同样难能可贵的是,雨果对中国艺术的高度审美觉知,他在信中将圆明园作为偏于幻想的东方艺术的至高代表,与偏于理想的西方艺术代表——巴特农神庙相提并论,并将两者视为艺术的两大来源。事实上,在其先前的作品《趣味》中,雨果就曾断言:“此为‘太阳神’,彼为‘中国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十分熟稔,2023年法国拍卖行惊现雨果亲笔注释的《道德经》抄本,他在“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旁批注道:“老子早于孟德斯鸠两千年提出治国智慧。”
这种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爱乃至痴迷,集中体现在雨果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上。逃亡暂居在根西岛期间,雨果先后48次购买中国艺术品,为此共花费了3000多法郎。要知道,他给情人朱丽叶买下的公寓,也才花了14000法郎。为了精心打造两人的爱巢,雨果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亲自为朱丽叶的“高城仙境”设计装修,还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中国风物件都一股脑地汇入其间,比如花瓶、乌木家具、宫灯、佛像,等等。终于,雨果为朱丽叶打造出一间富有奇异东方元素的“中国客厅”。面对雨果的这件“中国风”礼物,朱丽叶感受到她从未体会过的、繁复夹杂陌生的华丽感,她完全被迷倒了,并由衷赞叹道:“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在此,雨果俨然化身为一位装饰艺术家。
1902年雨果百年诞辰之际,巴黎市政府将位于孚日广场6号的公寓辟为雨果故居博物馆。朱丽叶的“中国客厅”里大部分物件和装饰品,连同雨果在其他住所的一些重要收藏品,都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馆,这栋三层建筑的二楼就囊括了令无数中国游客啧啧称奇的“中国客厅”。这间“客厅”的中央悬挂着中式宫灯,上绘仕女图。墙体及天花板布满漆着深深暗绿色的木制嵌板,两幅四尺中堂绘制着《四游记》人物。各类瓶、杯、碗、碟、盘等瓷制摆件,都被巧妙安放在雕刻着兰、竹、梅、凤等图案的橱柜上。最让人惊叹的是,是雨果镶嵌在墙壁上的大约60个瓷盘所构成的盘子墙,它们有如排山倒海之势,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暗绿色的墙体,贴合其上的洁白瓷盘,如群星般光芒闪烁,这美丽摄人的夜空,大概就是雨果心中所谓幻想式的东方艺术极境吧。

雨果故居博物馆中的“中国客厅”
纵观历史,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为数不少,但能达到雨果这般境界的,恐怕十分罕见。从17世纪开始,欧洲曾狂热地流行起“中国风”审美,甚至还创造出一个法语单词——Chinoiserie专门与之匹配。中国风和洛可可艺术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的西方人对装饰艺术的一种新潮认知。事实上,到19世纪中叶,装饰艺术上的中国风已然退潮,但雨果依然坚守着他的东方情调,甚至还创作了57幅“中国题材画”,其中的38幅木板烙画,密集悬挂在“中国客厅”的墙上。在此,雨果画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有当官的、乘船的、杂耍的、遛狗的、挑担的、做梦的……种种样态,都被雨果以可爱的喜感呈现,这些人物往往是洋葱一般的头、倒八字的眼睛、天真开朗的笑容、神秘莫测的表情……雨果对充满新奇而纯真的东方趣味的想象尽在其中。
1877年的一天,雨果的女仆不小心把他心爱的一只中国花瓶打碎了,75岁高龄的雨果立刻写了《粉碎的花瓶》一诗。诗的起兴可谓惊心动魄:“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被打得粉碎!”这是他“绝无仅有的花瓶”,是“难得一见的奇迹”。联系到中国花瓶是瓷器,在法文里“瓷器”和“中国”是同音词,雨果分明是在感叹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下的山河破碎,再联想到《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对英法联军暴行毫不留情的声讨,我们就更能体味到诗篇开头处这个绝妙双关的沉痛与悲凉。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